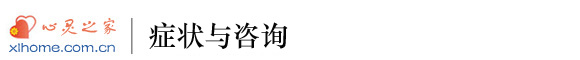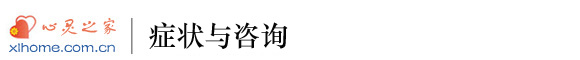抑郁是负面情绪相互助长、沉溺的结果。抑郁者体验着深刻的无助和绝望,这是不断重复的灾难化思维所至。想到自己的遭遇,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辜,而这世界又是那么残忍。眼前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,而自己只是一个被抛弃在荒漠里的孤儿,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死亡的到来。这时,他人的一举一动,事态的任何一种变化发展,都会被解读为于事无补而失去了意义。于是,更深刻的绝望袭来,这是一种希望的彻底幻灭,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一般,因为这希望承载着他生命的意义,当意义消失,生命之光也就随之陨灭。
抑郁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状态。好像所有的生命力都指向毁灭,所有关于生的信息都变得无意义。这股强大的奔向死亡的力量,既是对生之世界的否认,也是对自身存在的否认。如此强大的力量来自何方?它原本被灌注于何处?任何一种绝望都源于希望的幻灭,这希望就是生之梦想,是这股毁灭之力原本附着的地方。
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对生命的梦想,梦想是一个路标,朝着这一方向行进的每一步都是生命的意义。而抑郁者的梦想却有所不同,他们渴望把握和确信它是真实的存在才能生活。一旦对是否把握失去安全感,就会陷入崩溃。需要把握的东西被赋予等同于生命意义的重要性,失去了它,活着就只是行尸走肉。这些东西可能是自己的健康,也可能是某个重要人物的爱,某种人生目标,或者某种与安全、价值相关的感受等。他们内心的信念,以及建构于这些信念之上的情感体验,将这些东西与生命意义联结起来,文化背景、成长经历、教育方式等都可能成为这些信念的来源,从而形成抑郁者独特的人格结构。这种人格所遵循的逻辑常常导致灾难性的思维,使人极易体验到绝望和毁灭性的恐惧。
“如果我失去了这段婚姻,就失去了一切。”“如果我不能与人轻松地交谈,就会永远被别人看不起。”“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,活着有什么意思?”在这里,完美的婚姻、轻松地交谈、公平的世界,这些人们对生活的梦想与期望被当成了生活的必要条件,个人有意义的情感体验也依赖于这些条件来实现。一个由于紧密的家庭关系才获得安全感的人,在情感上依附于这种形势,失去婚姻生活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;而一个因为家庭暴力随时处于紧张状态,几乎没有轻松地与家人交谈的孩子,会误以为轻松交谈是体验融洽和爱的唯一方法。当这些被认为是获得安全和爱的唯一途径受阻,生活也就被摧毁了。
抑郁者的生命力可谓命悬一线,岌岌可危。因为这唯一的生命线被寄予理想化的期望,它必须是完美和安全的。身体必须是完全健康的,世界应该是公平的,婚姻就应该白头到老。只有当现实中,这些理想化的要求成立,生命才可以继续。就像婴儿不愿离开完美的子宫一样,理想化要求在现实中的挫败,会使抑郁者陷入毁灭性的恐慌,对现实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愤怒,因为“童话世界”幻灭了,他们既不能生活在幻想中,又不能生活在现实中。
通过确信所幻想的来获得安全感,原本是婴幼儿理想化的防御机制,它有效地给柔弱无助的个体带来继续生存的信心,通过虚构环境、他人,来构建一个夸大的、全能的自我。就像儿童进入童话世界一样,虚构的世界又能带给夸大自我以极大的满足。这在生命的早期,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机体的各项功能逐步完善,个体开始在认知、情感、意志等方面具备面对现实世界的能力,从而逐渐放弃理想化的防御。而抑郁者正是这一发展过程受阻,使他们认为可以生活的世界,始终蒙着理想化的面纱,面纱背后是“狰狞”的现实。当幻想还可以欺骗他们时,他们是愉快而兴奋的,一旦不小心揭开面纱的一角,他们会立刻陷入抑郁,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痛苦。
其实,天堂和地狱都源于孩子般的幻想。当没有了天堂,地狱也就不存在了。记得有一篇童话叫“小马过河”,不同身量的动物所建构的河水深度不同,内心感受也不同,有的乐观,有的恐惧。小马抛开这些固有的论断和想象,用实践建构了自己对河水的感受——不深也不浅。现实也是这样,当抑郁者修通了情感和认知,通过实践建构起新的对现实的个性化体验,他们会发现,人生是一个舞台,虽然总有谢幕的那一天,但仍然可以精彩地演绎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。